校友

作者简历:
唐晓峰 1948年生于辽宁海城。1972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75年毕业,后到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工作。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地理系研究生班,学习历史地理学,导师侯仁之。1982年留校任教。1986年至1994年到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1995年返回北大任教至今。现为北大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联系方式:
唐晓峰txf@pku.edu.cn
一本40多年前的讲义
在我珍藏的书册中,有一本侯仁之先生命我存阅的《战国秦汉考古》讲义,这是俞伟超先生在“文革”中编撰的,距现在已经40多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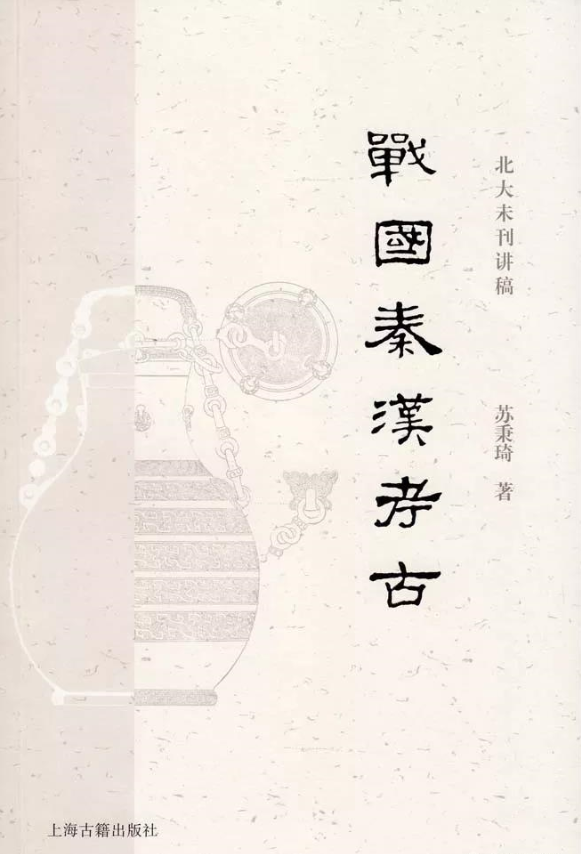
在这本讲义封二的左下角,有侯先生竖写的三行小字:“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首都医院体检之后,伟超同志送来。”文字所记,乃是两位先生学术交谊的一个瞬间情景。每读之,先生们的身影便会浮现眼前。
我们都知道,两位先生的学术交谊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那是去内蒙古和宁夏两自治区之间的乌兰布和沙漠地区做考古学与历史地理学的联合考察,发现了汉代的临戎城址、古井、高粱遗存、汉墓、鸡鹿塞遗址、干涸并沙化的屠申泽等等,其后他们共同署名发表文章,论证了这一带从早期汉代垦区变为晚期干旱沙区的历史。这是一次典型的跨学科合作研究。不过,让我觉得更有意味的是,两位先生的那番合作,冥冥之中,竟命定了我的学术生涯。换句话说,他们开出了一条学术新路,而我便是后来踏上这条路的一名学生。
我是1972年春天进入北大,在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这是考古专业在停顿数年之后的首次招生,大家可以感到老师们的兴奋,考古界的前辈也接连到班上看望,如夏鼐、苏秉琦、王冶秋等,其间还夹有美国的费正清,他由周一良先生陪同,来听了一次古汉语课。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我感受到每一位老师在重新进入专业教研时候的那种——仍然有几分压抑着的——热情,他们把这种热情尽力付诸在对学生的教学之中。首当其冲的是吕遵谔先生的旧石器时代考古课,讲得大家兴味浓浓。随后的新石器考古学、商周考古学,均为中国考古学大营的重镇,在此淬厉一过,才开始明白考古学是什么。再后是汉唐考古学,题目纷呈,难以招架。
我们当时并没有马上意识到,给我们每日上课,并不时到宿舍来与我们聊天的老师们(那时历史系的办公室与学生宿舍都在36楼),都是学界待机而发的猛将,如果只讲当年他们的所谓“职称”,今天的人便不会在意,但他们无一不是后来二三十年间学术高潮中的领军者。经过老师们的一番培灌,这班原来并不喜欢考古的绝大多数同学,也都成为忠于职志的考古工作者,并以此自豪。
俞伟超先生讲授的战国秦汉考古,最适我的偏好。尤其是一次,推行以专题形式带动学习,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俞先生给我布置的题目是:东汉墓葬中出土的买地券研究。
“买地券”属于冥契,代表死者领有阴间土地的凭据,在东汉丧葬中,此物相当流行。东汉道教创立,买地券颇受浸染,有许多道教观念,它们是反映当时社会风气、民间思想的直接材料。我喜欢的题目类型是:物——人——思想三个层次贯通,买地券的问题正好具有这个特点。
俞先生指导,从读材料开始。开头的几次,每讲完,便把几册抄录资料的笔记本给我,那是他历年搜集的资料,一册设一个门类,每事求多方对勘。一册一册读下来,思路遂一层一层展开。我不知道俞老师还有多少这类的笔记本,也不知道天下还有几位老师肯把自己辛勤搜集的、未曾使用过的“预备资料”,一股脑地交给学生。
虽然学生不才,这个题目做得并不如意,但俞先生从题目的开设到方法的身教,已让我学到了十分可贵的东西。此外,俞先生为人之热情,对学生勉励之诚恳,也令我们感动,有些同学离开学校后,仍然是俞先生的忘年挚友。
1975年春,我们班的一个小组到湖北江陵纪南城(战国时期楚国的都城)遗址做考古发掘实习,是俞伟超先生带队。那次实习,我们充分领略了城市考古的复杂性。探方布点要有讲究,而手铲下面出现的土层迹象,又有多种意想不到的可能,所以观察判定一定要要谨慎、灵活。还有,环境,我们北方同学习惯于干湿适中的中原黄土,而纪南城是在南方的水网之中,我们的探方常常渗水,水中居然还跳进了小鱼。这倒是让我们获得了对于历史城市环境差异的直观经验。
不过,水多的地方对于考古,也另有好处。俗话称:东西在土里,“湿千年,干万年,不湿不干就半年”。许多文物,甚至古人的尸体,在南方地下水的浸泡中,真的千年不毁。在那次与湖北省考古学家一同开展的江陵实习中,所发现的凤凰山168号汉墓,就是一个“湿千年”的例证。墓中的遗物大多完好,里面长眠了两千来年的遂少言大夫(名遂少言,爵位五大夫),也是肤肌全在。能发现如遂少言这样的历史“遗人”,机会是很少很少的。
那次湖北江陵实习,南方田野中盛开的油菜花,晚间飘忽的萤火虫,纪南城高大的城墙遗址,同学们愉快的情绪,还有俞伟超先生在工地上忙碌的情景,一切都令人难忘!
1975年夏,我自考古专业毕业,回到插队的内蒙古自治区工作。由于某种原因,我进入了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编辑室。北大老师不同意我脱离专业,吕遵谔、俞伟超先生先后写信来。内蒙古大学的贾洲杰,一位1958年北大考古专业毕业的老同学,一番努力,把我调到了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的考古组。这样,我算归队。
读内蒙古地区的考古文献,读到《考古》杂志上侯仁之、俞伟超合写的《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这是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研究。当时的感觉是:似曾熟悉,却实在新鲜。考古遗址以及那些司空见惯的汉代陶器残片,竟然变换角色,成为环境演变、历史时期土地沙化的力证。侯仁之先生的名字在考古刊物中的出现,也令人感到有些新奇。
1978年春,恢复招收研究生。我的目标自然是报考俞伟超先生的秦汉考古方向,但得知,那年考古专业招收的研究生,只设两个方向:旧石器、石窟寺。我对这两个方向既兴趣不足,又能力不备。可我又不愿放弃这次返回北大再学习的机会。于是,我想到了与俞先生并肩考察的侯仁之先生,想到了已经并不陌生的历史地理学。我顺利地通过考试,被北大地理系录取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生,师从侯仁之先生。
报到的日期是1978年9月,而7、8月间却接到侯先生的信件,唤我们马上到安徽芜湖铁山宾馆集合,参加芜湖地区的考察实习。我们三个研究生,还没注册,却要亲炙教诲了。
那次芜湖实习,是参加北大地理系承担的芜湖市整体规划工作。北大地理系里人文、经济地理专业的老师,可以说是全员到场,他们热情睿智、情绪饱满、勤奋工作,芜湖地区的一切都成为每日热议的学术话题。这样一种气氛是我从未领略过的,它正显示了当时的“时令”特色:“科学的春天”。
我们这个小组的任务是考察芜湖城市历史发展的区域特征,为整体规划提供历史依据。我曾参加过考古田野实习,但历史地理考察与考古调查不同,考古调查以遗迹、遗物为中心,而地理学要求观察大地上所有的地理要素,并结合主题——城市历史发展的逻辑,确定关键要素与不同时期城市的组合方式。在现场,一切要素俱在,就看你能提炼多少,就看你能否洞识它们之间的暗中关系。侯先生指导的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的考古学知识居然在芜湖考察用上了。一天,我们借了几辆自行车,按照侯先生的判断,到清弋江上游的丘陵区去寻找古城遗址的线索。在一处土围子模样的岗阜间,发现了考古课上印象极深的绳纹陶片,这是古代遗址的重要线索。侯先生第二天亲自来复查,继续有所发现,终于,确定了这处古城遗址的存在。(后来这座遗址得到正规考古发掘并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我至今记得回程时的情景,那天下午细雨连绵,土路泥泞,我们便觅得一只船家的小木舟,顺青弋江而下,一路谈笑。侯先生见大家衣衫湿凉,便提议:回去喝些酒怎样?我们顿时欢呼,酒不仅驱凉,更要庆功!
芜湖历史地理的考察研究以一长篇研究报告结束,当地的湖沼、河流、岗丘,以及人类借助环境所进行的各类活动,当然,还有考古遗址,悉数纳入城市的历史范畴。以如此综合眼光来关注城市的发展,对于我们几个历史地理研究生来说,是具有根本意义的学术视野的开启。
工作后期,安徽师大邀请侯先生去作报告,讲芜湖的历史地理。以侯先生的声望,报告场面很大,主会场地方不够,还设了分会场,分会场悬挂喇叭,就坐的都是“听”众。以学术角度讲解地方历史地理,是历史地理学者们所做的一项很受欢迎的活动,可以说,侯先生是这种活动的开创者。当年北大的同学,不管是哪个系的,大多记得侯先生关于北京历史地理的精彩演讲。“那时候凡是新生入学,都去大礼堂听侯先生讲课,讲的好极了。……不但新生去听,有些老学生,听过了还去听。侯先生讲课有一很大特点,逻辑性非常好,思路清晰,语言非常好,听得你没办法做笔记,因为听得你忘了做笔记。”(李保田,北大1957级学生)这次在安徽师大的演讲,不用说,也是这样的场面。
其实,面对大众的历史地理学的讲座之所以受欢迎,不仅仅是因为演讲者的深入浅出或语言生动,更重要的,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科学思维,它突破常识,破解传说,为地方历史提供了一种新鲜的观察角度、历史证据、论述逻辑。一些当地人熟悉的地理现象,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所产生的复杂的社会功能与曲折的变迁过程,常常是他们没有想到的。他们会吃惊地反应:我的家乡原来是这样的!当年,我在内蒙古阅读侯先生、俞先生关于乌兰布和沙漠的研究时,就有这样的感受。
1978年9月份,我们正式到校注册、开学。侯先生的第一课没有选在教室,而是在圆明园遗址里面上的。那时的圆明园遗址区,还没有建成公园,到处是野趣,随意进出,而在侯先生眼中,这正是一个历史地理研究的现场。那一天,圆明园遗址中的丘山湖湾、基址残垣都浸沐在秋光的金色之中,这本是我熟悉的地方,曾多次结伴来这里窜游。而现在,在侯先生的讲述中,我才意识到,山前荒野改建为皇家园林,这是北京历史地理研究中一个严肃的专题。
圆明园的匠心设计,本在山水布局,水的灵动体现活力。而圆明园的水,却不是自然而然的获得,在其背后,有一个人类智慧与技术的投入。历史上的水利专家,踏遍西郊原野,斟酌山泉水量,精心设计了一套体系,才解决了京城数百年来的水源难题,才能保证圆明园福海辽阔湖面的平稳和大水法众多喷泉的欢腾。侯仁之先生在燕大求学期间,便开始考察西郊水系的遗迹,查阅文献,访问乡民,最终,彻底搞清了北京水源的历史地理,写出著名论文《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
圆明园以及西郊地带,是侯仁之先生终生从事的历史地理研究的起点,他带我们到这里来,上第一堂正规的课程,其意义是很明显的。
在燕大读研究生期间,侯仁之先生曾应导师顾颉刚的委托,组织京郊的古迹古物调查实习,想必大地上的这些遗存,给热爱地理学的青年侯仁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多年后与俞伟超先生的在现代科学水准上的深度合作,则最终完成了学科发展的跨越。
经过实践与思考,侯先生对历史地理学与考古学的结合做了认真的总结和倡导,1973年便撰写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与文物考古工作》一文,他发自内心地写道:“作为一个历史地理工作者,我深切感受到,在探讨现代地理环境的演化过程中,如果没有文物考古工作者参加协作,许多关键性的问题就很难圆满解决。”“有一些古迹文物,如果只是孤立起来看,或许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历史价值或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但是如果把它和有关的事物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就常常有助于解决一些除此以外还难于解决的问题。”“各有关学科之间,由于实际的需要,也逐渐走向互相支援、互相协作的道路,并促进了一些边缘学科的成长。”
1981年夏,我研究生毕业,所做的论文是《从考古发现论证北京城成长的交通条件》,从此以后,考古与历史地理便成为我学术知识的两大支柱。而像我这样的,以考古与历史地理的结合为治学之道的人,在全国各地是越来越多,许多人都做得很好。
想象40多年前,侯仁之先生从俞伟超先生手里接过这份讲义后,定是十分珍重,才专门写下那几行字。侯先生有一个习惯,得到重要的书籍,都要在书上记下缘由与时间。
这份讲义,见证的是先生们的友谊,属于他们,也属于北大,属于那个年代,当然,还属于前者开拓、来着相继的学术事业。
(2017年4月1日于五道口嘉园)
